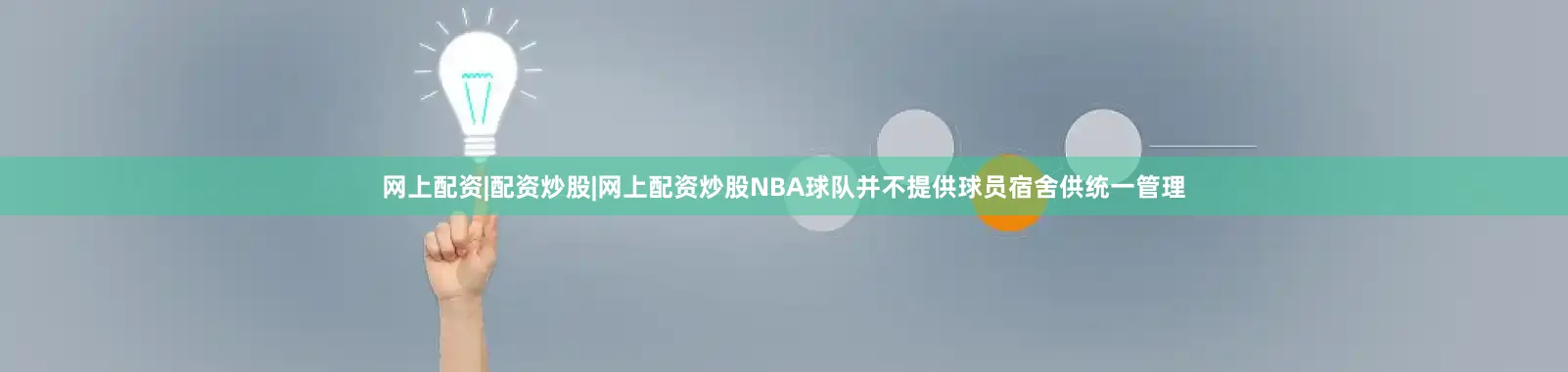今年夏季的雨水不多,入秋了反而多了起来。在窗外有雨的一天,我陷在躺椅上听李诞的播客,他讲起有一年和陈丹青坐在敦煌石窟对面的山坡上,一边喝酒一边聊天。
聊到生与死的话题,说起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死亡的体验。
我开始回想,对我来说,近距离的接触死亡是什么时候。
没想到,我首先想起了很少忆起的舅舅。一回忆,就刹不住车。从我几岁开始到三十几岁,和舅舅相处过的画面,像电影片段一样清晰地出现在眼前。
他已经走了六年,走的那天,正在上班的我接到了电话,说舅舅不行了,快来。
我赶紧打车,路上还没反应过来,在我的认知里,糖尿病、高血压这些病虽然不轻,但离死亡还是有段不小的距离。
走进病房时,我看到他静静地躺在床上,像是睡着了,嘴角到脸颊上,有一道刚拔掉管子带出来的鲜红的血迹。
身旁的监护仪没有显示数字,既没有象征着还活着的曲线,也没有电影里常看见的象征着死亡的拉平的直线。
我看着身旁也在错愕中的长辈,问:“这是,走了吗?”长辈不语。
展开剩余90%在舅舅之前,我经历过姥姥、姥爷和爷爷的去世,等我到场时,他们都已经入了棺。
我没有见过,还躺在病床上像睡着了一样的死亡,没有经历过,发生在我到场几分钟之前的死亡。
我看向他那和往常并无异样的黝黑的手,我把手从他拇指和食指之间的缝隙里伸进他的掌心,触摸到那粗糙的一道道清晰可见的皱纹,没有冰冷。
当天夜里,他被推进殡葬馆整理遗容,我和家人们分散地坐在馆外的马路牙子上。
漆黑的夜与殡葬馆的灯火通明形成鲜明的对比,黑暗中每个人都一言不发。
整理好遗容,我进去看他,嘴角的血迹已经没有了,我从没看到他如此舒展如此干净的脸。印象里,他的脸总是黑黑的、油油的,显得很脏。
那个等待的夜里,我像今天此刻一样,回顾了他整个一生,那时我就想为他写下一些话,作为他曾经来过这世上的留念,但很快我就回归了惶惶的日常里,书写就此搁置。
我也没想到,六年后的今天,我会再次想要把他此生写出来,而那过往的一幕幕,竟未曾因为过了六年而变得模糊,反而忆起了更多、更具体、更清晰的故事。
他是我的大舅,在六个兄弟姊妹中,他排行老二,上面还有一个姐姐,也就是我的大姨。作为家中第一个儿子,我想他也许有过幸福的幼儿时期。
三四岁时,他的奶奶,也就是我的太奶奶,从乡下来到城里的儿子家,临回时想带走一个孩子回乡下养。
那个年代亲人间过继孩子不是新鲜事,当老人的开口想带走一个孙子兴许是大人间觉得更正常的事。
那时,太奶奶其实本想带走我的大姨,无奈大姨生性调皮,看太奶奶要带走她更是上蹿下跳,真就让老人家觉得这孩子不好管教,于是选了听话懂事的老二,我的舅舅。
儿时的他不会知道,听话这个看上去的优点让他的人生从此走上了不同的路。
这一走,就是十几年。直到他十几岁,太奶奶去世了,他才回到城里的家中。
后来,他不止一次地跟我们这些小辈讲过一个丢笔的故事。说是有一年冬天,外面冰天雪地,他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丢了唯一的一支钢笔。
他沿路找啊找,就是找不到。丢笔已经很沉重了,更令他害怕的是不知如何回家面对太奶奶的惩罚。
果然,太奶奶看见他空着手回了家,在那个年代竟然丢了这么珍贵的钢笔,很是生气,于是罚他跪在雪地里反省。
听话的他,就真的跪在雪地里。
他说,他跪了一夜。我不知道他究竟跪了多久,也许没有一夜,因为哪怕只有一小时,那透骨的寒冷和愧疚、难言的境地也足以让一个孩子度日如年。
也许,真的就是一夜,因为从此他的膝盖落下了一生的病,走多点路就会一瘸一瘸的,爬个楼梯总要歇好几回。
可能是最该长身体的年纪吃了太多苦,他是兄妹六个里个头最矮的,又矮、又胖、又黑,再加上与其说是老实本分不如说是木讷的性格,说个话都磕磕巴巴的,我们这些小孩会觉得他傻里傻气的,也不像对其他长辈一样那么尊重他。
他也不在意,也许他就是脾气好,也许是一种钝感力,大部分时候都只是乐呵呵地看着我们闹。这就助长了我们的嚣张气焰,有一回玩笑开过了火。
那次应该是过某个节日,一大家子二三十口齐聚姥姥家。姥姥家的厨房是个小木屋,开在室外的楼梯拐角上,大人们轮流在里面炒菜。
后来轮到大舅进去,我们几个不知轻重的蹑手蹑脚地从门外把插销插上,把他反锁在了小木屋里。然后慌里慌张又不敢声张地跑回了家。
刚进家,就听见小木屋那边传来巨大的闷响,一声,两声,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,看着同样面红耳赤的表姊妹们默不作声,像等待从山上滚下的巨石落地。
终于,咚,第三声响过,这一声跟前两声不同,带着木头撕裂的粗糙感,大舅把整个厨房门踹了下来!
先看见门被踹开的是姨妈,她快步往家走,还没踏进房门就吆喝开了,“谁把大哥锁在了厨房里,给我出来!”
我们几个再没了方才锁门的恶作剧窃喜,因为大舅那敦实的一轻一重的脚步正靠近我们。
我们心想,这回完了,都说老实人不轻易发火,发火就是个重量级的,这顿揍是免不了了。
大舅进来后,气呼呼的,但是他并没有冲着我们发火,而是冲着其他大人们吆喝了一顿,用他这辈子最愤怒的语气夹杂着时不时出现的结巴,把我们抱怨了一通。
这个画面很奇怪,肇事的我们就在眼前,但他不直接骂我们,也不看我们,而是对着他的兄弟姊妹和爸妈,用“他们把我锁起来,太气人了”这种曲线骂人的方式,间接地制裁了我们一下。
多年后我再回想这个画面,我想,一是他不舍得揍我们,二是那刚刚的三脚踹门已经发泄了他绝大部分的不满,甚至也许,夹杂着他前半生的不满。
回顾他一生,我都没再见过也没听说过,他还发过比这次踹门事件更大的火。
不过,虽然他没揍我们,自那次起我们也老实了,知道了把老实人逼急了的威力,不敢再对他造次,好长一段时间都对他毕恭毕敬,每次路过被重新镶上的厨房门时都得心惊一下子,生怕门突然被什么大怪物给撞开。
别看他木讷又不善言辞,可他并不是笨,相反他是六人当中学习最好的,也是唯一有铁饭碗的。
姥姥家的书除了我们小孩的几本图画书,剩下能见到的书都是舅舅的。而且,都是扔出去能砸死人的大部头。
我记忆里对他的画面,很多都是他在读书的样子,头埋在书里,手在做笔记,嘴巴里还在念叨着什么。
有时我看到他在家里读书,有时我们几个孩子放假时跟着他去他工作的科研所,他一边或是读书或是做什么研究,我们一边无所事事地摸这摸那。
他什么书都读,自学能力很强,医学、科研、英语、各种,还经常抱着书过来跟我讲两句他的所学。
在姥姥家所有的孩子里,我也算是大人眼里“最听话”的,也是矬子里拔将军才比较出来的愿意读书的那位,所以在大舅这里,他就觉得我是个能学习的好孩子。
他退休后,要把科研所里的一些书处理掉,他专门从所里抱回来一本扔出去能砸死人的辞海送给我,说,他觉得我能读这个。
看着这本印于1989年、2500多页、这辈子我拥有的最厚的、最有逼格的一本书,我笑纳了。
那时候,我不会想到,没过几年他就会离世,这本书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遗物。
这么些年了,我一次也没读这本书,不过我带着它,搬了好几次家,如今在安顿下来的书房里,给了它一个高高的书格的位置,能俯瞰我所有的书籍。
舅舅一生未曾娶妻,无儿无女。
小时候我会觉得他的外形和木讷让他不太容易找对象,但后来我意识到,更多的可能是,他不怎么想找。
他三十来岁时,曾经有一次距离婚姻最近的机会,但是他却拒绝了。
那是从老家来的一位姨,在姥姥家住了一段日子。我记不清她的脸了,但能清晰的记得她带给我的感受:淳朴,一看就是踏实过日子的人。
不久以后老家亲戚在中间说媒,撮合这位姨和我大舅,我知道是姨看好了舅舅。
家里人都觉得这再好不过了,恨不得替他点头,可没成想,他断然拒绝了。
这位姨后来又来过姥姥家几次,可能是想再争取一下,但可以想象一个老实的木讷的人做出拒绝的表态时,会是多么地生硬又没有回旋之地,这事自然就不了了之了。
直到舅舅四十好几了,我都还经常听我姥姥埋怨他,嫌他当时不知好歹,要是那时结了婚,孩子都老大了。他就嘿嘿不语。
我不知道,后来姥姥姥爷相继去世后,他在世上再没有了家的归处时,是否曾后悔过当初的选择。
也许,他没有后悔过,因为,他确实喜欢过一个人。
这事,在这世上应该是只有我和我的表弟知道,但我不确定表弟现在还记不记得,如果他不记得了,那我就是唯一知道此事的了。
那年假期我和表弟基本驻扎在他的研究所,跟着他上班下班。有一天,他主动地神秘兮兮地问我们:“你们看看,那个人怎么样?”
我俩顺着他视线看过去,一个女子的背影。我想当时我是看见了她的脸的,但如今我完全想不起她的面容,我想不是因为面容美的不够印象深刻,而是背影就足以打动人了。
长发齐腰,白色过膝裙子,阳光洒下来在她的背影周围形成一圈光晕。
我弟立马心领神会,问:“你喜欢她?”舅舅没说话。然后我弟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替舅舅去表白,我的记忆就戛然而止在这里。
我不记得我弟有没有代舅表白,舅舅有没有自己去表白,但从不了了之的结果上看,这不是一场无疾而终的暗恋,就是表白被拒的结束。
但是,就像虽几十年过去了,每当我回忆起这位阿姨的背影仍会禁不住微笑一样,我想在后来舅舅漫长的人生中,这少有的甚至是唯一的爱慕之情也一定一次又一次地给过他温存。
爱情不是舅舅这一生的主题,和姥姥姥爷的相爱相杀才是。
从他十几岁从乡下回了家,到姥姥姥爷相继去世,他一直生活在这个家里。
其他五个兄弟姐妹都是逢周末或节日才来,所以大部分时候,这个家像是一个三口之家。
而这个没有结婚没有子女的大儿子,在我姥姥姥爷的心目中,好像还是一个孩子,哪怕他都三四十了。
而舅舅也是,一到了姥姥姥爷面前,仿佛也回到了十来岁。
他们之间常常为点小事呛呛地脸红脖子粗,而争执起来的样子,跟当时十来岁的我跟我爸妈争执时并无两样。
他也没怪过姥姥姥爷把他一个人送出去那么多年,相反,我觉得他很爱他们。
现在我十几岁的大女儿都开始不太叫我“妈妈”了,而代之一个轻描淡写的“妈”。
但舅舅一直用叠词喊我姥姥“妈妈”,而且音调也不是普通的一声加轻声,而是三声加二声,就是差不多“马麻”的发音,叫我姥爷是“把拔”。
我每次听见他这么叫他们,我都头皮一阵发麻,但是他喊得极其自然,姥姥姥爷也接收得极其自然。
这声不同的“爸爸”“妈妈”,像我的八岁的小女儿跟我撒娇的亲密无间的样子。
他们就这样相爱相杀了一辈子,我常看到的画面就是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在吼五十多岁的大儿子,大儿子会据理力争地说“马麻,你听我说。”
舅舅火化后,跟姥姥姥爷合葬在了一起,墓碑上写着他们三个人的名字。
从小离开父母的舅舅,死后成了唯一一个可以跟父母永远呆在一起的孩子,享受着父母独一份的、永远拿不走的关爱。
每次去上坟,我就对着他们三个人一起祭拜,我跟姥姥姥爷许许愿,再跟大舅许一遍巩固一下愿望。
《寻梦环游记》里有这样一段话:
“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点,遗忘才是。如果在活人世界里,没人记得你的话,你就会从这里消失,我们称之为最终的死亡。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在没有一个人记得你。”
每个普通人的平凡一生,回顾起来,都是一部史诗。
谨以此文,记得我的舅舅。
发布于:山东省垒富优配-配资公司-证券配资门户-低息股票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股票十大平台我们迟早需要让其他球员也获得更多的信心
- 下一篇:没有了